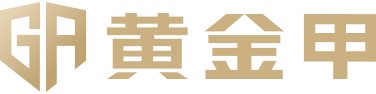上海滩的夜总来得急些,华灯初上时,法租界一栋洋楼的客厅已亮起暖黄的光。黄金荣斜倚在沙发上,指尖摩挲着一只蜜梨的纹路——表皮泛着琥珀色光泽,像浸了蜜的玉,在灯光下透出温润的质感。

“大帅,杜先生派人来报,今晚‘货’的路线被巡捕房盯上了。”副官站在门边,声音压得极低,生怕打破这份静谧。
黄金荣没抬头,只抬了抬下巴:“让他再等等。”
他拿起桌上的银刀,刀刃在灯光下闪过一道寒光。这把刀是他早年走江湖时用的,削过无数人的骨头,也削过无数次梨。如今刀锋依旧锋利,握在手里时,却多了几分温润。
梨皮顺着刀刃缓缓卷起,像一条金色的丝带,落在青花瓷盘里,叠成小小的山丘。果肉露出雪白的肌理,甜香瞬间弥漫开来,混着烟草味,在房间里打了个旋儿。
“大帅,您怎么还亲自削梨?”副官忍不住问。他跟了黄金荣十年,从未见过这位大佬为任何人做过这种事——哪怕是杜月笙来访,他也只是让人端一盘现成的。
黄金荣笑了笑,手指轻轻划过梨核:“你不懂,削梨和做人一样,得有分寸。外头的皮,该剥的要剥干净;里面的肉,得留得匀称。”他说着,将削好的梨递给副官,“尝尝,今年的梨比去年甜。”
副官接过梨,咬了一口,果然甜得发腻。他抬头看黄金荣,却发现对方正望着窗外的梧桐树,眼神有些恍惚。
“那年我在苏州学手艺,”黄金荣突然开口,“师傅教我削梨,说‘梨者,离也,但要削得干净,才能留住甜’。后来我进了青帮,杀过人,抢过地盘,可每次削梨时,总能想起师傅的话。”
副官沉默了。他知道黄金荣的过去——从一个街头混混,一步步爬到青帮龙头,手上沾满了血。可此刻的他,像个普通的老人,在灯下削梨,说着无关紧要的往事。
“杜月笙那边……”副官提醒道。
“告诉他,明天早上把‘货’送到码头。”黄金荣打断他,“今晚我要好好吃个梨。”
副官应了一声,退了出去。房间又静了下来,只有刀刃划过梨皮的声音,像一首古老的歌谣。
黄金荣将最后一口梨放进嘴里,甜汁顺着喉咙流下去,带着淡淡的涩。他想起当年在苏州的巷子里,师傅坐在门槛上削梨,阳光照在他的脸上,皱纹里都藏着笑。那时的他,以为削梨就是一辈子的事。
如今,他成了上海滩的大佬,手下几千号人,可每当夜深人静时,他还是喜欢削梨。不是因为它甜,是因为它能让他想起那些简单的日子,那些没有被权力污染的时刻。
窗外的风掀起窗帘,吹得梨皮在地上打了个滚。黄金荣弯腰捡起它,放在盘子里,然后靠在沙发上,闭上了眼睛。
或许,这就是权力的代价——你可以拥有整个上海滩,却永远回不去那个单纯削梨的下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