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的长江边,雾气还未散尽,老汉口租界的红砖墙在晨光里泛着暖调。我沿着黎黄陂路漫步,鞋跟叩击青石板的声音惊醒了巷口那只打盹的花猫。转角处,一爿挂着“老凤祥”铜牌的金店突然撞入视线——鎏金的店招下,木格子窗映着百年前的月光,仿佛时间在此刻慢了下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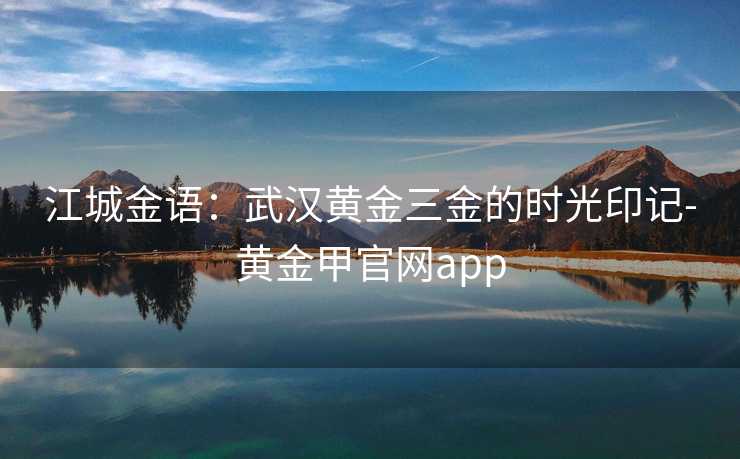
推开门,铜铃叮当,满室金辉流转。白发苍苍的李师傅正伏在錾刻台前,银簪划过金箔的沙沙声,像一首古老的歌谣。他抬头见我驻足,笑着递来一杯温热的菊花茶:“姑娘可是想看看‘老手艺’?”我点头,目光落在桌上的半成品——一枚金戒托上,錾刀正雕琢着缩小版的黄鹤楼飞檐,每一道线条都带着江风的味道。
“我们这行讲究‘三分料,七分工’。”李师傅摩挲着金块,指腹沾着金粉,“早年汉口的金店,从打金到镶嵌,全靠手工。你瞧这‘打金’,得把金条烧红,反复捶打成薄片,再剪成想要的形状……”他的话音未落,门外传来清脆的笑声。一位扎马尾的女孩抱着 sketchbook 走进来,正是如今在小众圈子里颇受欢迎的“90后”金饰设计师小雅。她举着图纸兴奋地说:“李叔,你看这个方案——把长江大桥的钢架结构和热干面的碗纹结合起来,做成项链吊坠!”李师傅眯眼看了看,赞许地点头:“到底是年轻人,把咱们江城的魂儿揉进去了。”
我忽然想起奶奶留下的旧金镯子,忙翻出照片请李师傅辨认。他戴上老花镜仔细端详,指尖抚过镯身隐约的纹路:“这是民国时期的‘水波纹’,当年汉口的金店常用这种样式,寓意‘财源如江水’。你奶奶怕是在武昌起义前后买的吧?那时候金饰不仅是首饰,更是信物呢。”原来,镯子内侧竟藏着极细的暗纹——一只展翅的鸽子,翅膀下压着“1911”的字样。奶奶临终前曾说,这镯子是她年轻时参加学生运动时,同志们凑钱买的,象征“和平与希望”。
离开金店时,夕阳正给长江镀上金边。我摸着口袋里的新镯子——小雅设计的版本,黄鹤楼与长江大桥交相辉映,镯身内侧錾着奶奶当年的暗纹。江风掠过耳畔,恍惚间听见百年前的铜铃声与如今的谈笑声重叠,那些被时光打磨的金饰,终究成了江城文化的注脚。
站在长江大桥桥头,看晚霞染红江面,我突然懂了:所谓“黄金三金”,从来不是冰冷的金属。它是老汉口烟熏火燎的记忆,是新青年天马行空的创意,是祖孙两代人的牵挂,更是武汉这座城,在岁月长河里写就的、闪闪发光的浪漫诗行。
